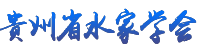水族文化研究中的放屁现象(韦友寿)
水族文化研究中的放屁现象
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韦友寿

图一 汉字“大”字演变

图二 商周铜器铭文“大”字

图三 水族文字“人”字
2021年3月7日,我在自己的QQ空间里发表了这样一条说说:“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资深教授万献初先生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师从王宁先生,主攻文字训诂学,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师从宗福邦先生,主攻音韵训诂学,深得章黄学派精髓,传统语言文字学功底深厚,言必有据,富有创见,授课深受学生欢迎。他提出治学八字箴言:‘敬畏学术,尊重元典。’在我看来,既然水汉同源,从事水族文化研究者,必须对水族语言与文化有原生体验,并深入学习中华文化元典(经、史、子、集),否则,仅凭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些皮毛知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根本没有资格来奢谈水族文化研究的!”发这条说说的目的,一是强调水汉同源,二是呼吁从事水族文化研究的人士多阅读中华文化元典。水族文化研究热心人士潘明江先生,把这条说说转发到贵州省水家学会群里去。万万没想到,这条说说引起了省内某位民族学研究权威专家的极大震怒,说这简直是放屁!既然权威专家喜欢说放屁,那我就从放屁说开去,谈谈水族文化研究与放屁的关系。
我首先申明,水族文化需要从多学科、多视角来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科学、正确的结论,否则容易误入歧途。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对于研究水族文化在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非常管用的,若要对水族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则无能为力,不但帮不上忙,有时候还添乱,所以还必须依靠历史学和语言学,否则是稀里糊涂,走进了死胡同,还不自知。
水族文化研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地开展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在我看来,由于脱离了历史学和语言学,仅靠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些水族文化研究权威专家们是找不着北的。说得委婉、含蓄一点,就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专家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走弯路、走错路。说得坦率、直白一点,就是专家们在陆陆续续地放了四十多年的屁,只不过,这些屁是分为土屁和洋屁而已。依靠田野调查,不进行过滤和筛选,完全相信民间传说者,放的是土屁。无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动辄援引西方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理论,挟洋自重,洋腔洋调,最终又不能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问题者,放的是洋屁。下面,我针对放土屁者和放洋屁者各举一个例子,以资佐证。
咱们先举一个放土屁的例子。1995年1月,省内某位水族文化研究权威专家在《贵州民族研究(季刊)》第一期(总第六十一期)上发表了学术论文《水族铜鼓舞探源》。该论文在直接引用陈远璋先生论著中“左江岩画的主体人像,无论是正面或侧身,多作曲肘举手,曲膝蹲腿的姿势,造型上下对称,恰似怒蛙伏地之状”这句话之后,接着说“就今天水族铜鼓舞蹈的动作来看,仍是保留了对蛙类动作的模仿,这是与古越人崇蛙观念有关的……因此,今天的水族铜鼓舞,实际上是古骆越人崇蛙观念文化遗留的具体体现。”恕我孤陋寡闻,在水族地区,从未听说有蛙崇拜,把蛙作为神物来对待。由于青蛙身材五短,大腹便便,眼睛鼓鼓,水族民众喜欢把具有这种体貌特征的人比喻为青蛙。由于青蛙喜欢在夏季集体鸣叫,所以水族民众把七嘴八舌、聒噪不休比喻为蛙鸣。在水族地区,大众场合,失控放屁,视为不雅,放屁者为化解窘境,消除尴尬,制造幽默,推卸责任,往往解释说这是蛙鸣。如果水族地区有蛙崇拜,水族民众还会有上述这些说法吗?这根本不值一驳!
这位权威专家为什么有这个误判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水族铜鼓舞与水族文字有关。水族铜鼓舞是由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化局原副局长宋晓君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于1984年荣获黔南州文艺汇演一等奖。该舞蹈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成功地融入了水族文字“人”字这一文化元素。
水语属于汉藏语系,与汉语有亲缘关系。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水族文字是用来记录部分水语的。部分水族文字对汉字的借鉴,非常明显,有迹可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笔画增损,二是姿势变换(主要体现为汉字的倒立、竖转、侧卧)。
汉字“大”字是个象形字(详见上图一),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象人的正面形,有手有脚。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大”字(详见上图二),象正立双手下垂、翻掌向外的人形。
“大”是汉字部首之一,从“大”的字往往与人类或人事有关。“大”亦作“亣”,《说文解字·大部》:“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亣也。”《说文解字·大部》:“亣,籒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段玉裁注:“大下云古文亣,亣下云籀文大。此以古文籀文互释,明只一字而体稍异。”
“天”字是个指事字。甲骨文中的“天”字,像正面站着的“人”形,突出头部,以示人之顶颠,义同“颠”(头顶)。金文“天”字更像“人”形,仍突出人头。天字上部象征人头部分的圆点,小篆变成一横画。因此,“天”字可以理解为“大”字头上添加一横。“天”字的本义是“人的头顶”,又表示人的头顶上方、日月星辰所在的太空苍穹。如《简易道德经》:“常言天,齐究何也?昊曰:无题,未知天也,空空旷旷亦天。”
“大”字和“天”字的构形理据,应该源于伏羲先天八卦。起初,伏羲创立八卦,以三画(爻)为一卦,下画(爻)象地,中画(爻)象人,上画(爻)象天,称为“伏羲八卦”“原始八卦”“先天八卦”。先天八卦的象征意义是天在上、地在下、人在中间。所以,“大”字的本义就是“一个人叉开双腿、垂下双臂,顶天立地”。
在古汉语里,“大”表示“中间”义。例如,《尚书·大禹谟》“民协于中”句下,西汉孔安国传:“民皆命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易经·大有卦》:“《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三国王弼注:“处尊以柔,居中以大。”近代高亨注:“象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大正之道。”后以“大中”指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
水语把“大”读如“dá”,国际音标拟音为[ta⁵⁵],用来表示“中间”,其字义也应源于伏羲先天八卦。“坉”字,“土”与“屯”联合起来表示“用土来围合”,汉语拼音读“tún”,用来表示“村庄、寨子”,水语读[tum³³],用来表示“处所、位置”。在横向空间位置方面,今天党政机关排会议主席台领导座次,当主席台人数为单数时,把领导职务最高者安排坐在最中间,该位置水语称为“坉大[tum³³ ta⁵⁵]”;在纵向空间位置方面,水语把“半中”称为“大半[da⁵⁵ pan⁵⁵]”。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语料,就是“以中为大”“大者居中”的有力例证。
在现代汉语里,“大”字主要表示“容量、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年龄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的对象”,与“小”相对。而水语则牢牢地保持着“大”字的本义“中间”,与“介”“方”“䂬”相对。
“介”字,《广韵》注音为“古拜切”,读如“盖”,汉语拼音读“jiè”,平话桂北片两灵小片宁远(清水桥)方言点读[kia⁵⁵],平话桂北片两灵小片龙胜(红瑶)方言点读[kai⁵²],都是用来表示“边、侧、畔”。例如,《楚辞·九章》:“悲江介之遗风。”《尔雅·释诂》注曰:“介,侧畔也。”。
“介”字,水语中的三洞土语区和潘洞土语区读[ȶiai⁵⁵],与汉语今音“jiè”较为接近;三洞土语区中的九阡、荔波一带读[ɣai²²],与中古音读如“盖”、平话桂北片两灵小片龙胜(红瑶)方言点读[kai⁵²]最为接近;阳安土语区读[kʰiak⁵⁵],与平话桂北片两灵小片宁远(清水桥)方言点读[kia⁵⁵]最为接近。尽管读音不尽相同,而意义则一,都是用来表示“边、侧、畔”。例如,水语把河边(江边)、河畔(江畔)称为“介㴸”。
查汉典网,“㴸”字今有三种读音“nà”“shǎn”“yè”,而字义则一。《康熙字典》:“《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失冉切,音陕,水動貌,一曰水流漂疾之貌。《木華·海賦》:㴸泊柏而迆颺。”《广韵》和《集韵》是北宋年间官修大型韵书,《韵会》即《古今韵会》,是元代黄公绍编纂的大型韵书,《正韵》即《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官修大型韵书。这些韵书都是从汉语的角度来对“㴸”字进行注音和释义的。再上溯历史,从古华语的角度来看,水族民众从古至今,一直把河流称为“㴸”。三洞土语区是水语三大土语区中之最大者,除水婆、水龙、塘州、天星一带读[ʔnie¹¹]以外,其余地区一律读[ʔnia¹¹];阳安土语区读[nia¹¹];潘洞土语区读[nie¹¹]。从音韵学角度着眼,可以把水语中“㴸”字的读音分成两组:[ʔnia¹¹]与[nia¹¹],[ʔnie¹¹]与[nie¹¹]。跟汉语读音“nà”相比较,[ʔnia¹¹]与[nia¹¹]多了个介音[i],这恰好体现出“古华语多介音”这一语言特征,而[ʔnia¹¹]比[nia¹¹]要略古一些,因为前者声母[ʔn]是个先喉塞音,比后者声母[n]先产生。[ʔnie¹¹]与[nie¹¹]是分别由[ʔnia¹¹]与[nia¹¹]演变过来的,主元音由[a]到[e],这是元音高化的结果。从声母来看,[ʔnie¹¹]比[nie¹¹]要略古一些,具体理由同[ʔnia¹¹]与[nia¹¹]。
水族民众从古至今,一直把河边(江边)、河畔(江畔)称为“介㴸”。三洞土语区中,大部分地区读[ȶiai⁵⁵ ʔnia¹¹],九阡、荔波一带读[ɣai²² ʔnia¹¹],水婆、水龙、塘州、天星一带读[ȶiai⁵⁵ ʔnie¹¹];阳安土语区一律读[kʰiak⁵⁵ nia¹¹];潘洞土语区一律读[ȶiai⁵⁵ nie¹¹]。针对“江边、江畔”,汉语称“江介”,是定语前置,水语称“介㴸”,是定语后置。定语后置是古华语的一种表达习惯,这种语法现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不乏其例,详见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出版)和赵平安《两周金文中的后置定语》(《古汉语研究》1999年02期)。
“方”与“旁”是同源字,上古音都读[paŋ],故“方”字可假借为“旁”字。例如,马王堆帛书《十六经·本伐》:“故圉者,䞠者也;禁者,使者也。是以方行不留。”《淮南子·主术训》:“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汉书·地理志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颜师古注曰:“旁行,谓四出而行之。方制,制为方域也。”《仪礼注·大射礼》:“左右曰方。”郑玄注:“方,旁出也。”《玉篇》:“旁,犹边也、侧也。”既然“旁”字有“边、侧、畔”义,“方”字当然也有“边、侧、畔”义。所以,今天在汉语里,“中央”与“地方”是一组意义相对的词语。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旁”字的近代音读[pʼuaŋ],“方”字的近代音读[fuaŋ]。在水语里,“方”字用来表示“边、侧、畔”义时,读[faŋ²²],与[fuaŋ]相差无几,只是丢失了介音[u]而已。
《康熙字典》:“䂬,《唐韵》《正韵》居竦切,《集韵》古勇切,并音拱。《说文》:‘水边石。’又,《集韵》渠容切,音蛩,义同。”《说文解字》:“水边石,从石,巩声。《春秋传》曰:‘阙䂬之甲。’居竦切。”“䂬”字,汉语拼音读“gǒng”,本义为“水边石”,水边的石头当然是位于江边、河边、海边,水语读[koŋ²²],引申为“边、侧、畔”。例如,水语把江边、河边称为“䂬㴸”,读[koŋ²² ʔnia¹¹]。由此可以看出,水族先民曾经长期在江边、海边生活过。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于公元220年覆亡。古华语分化演变时,汉朝应该尚未建立。所以,古华语就是汉语和水语的前身。上述语料,就是“水汉同源”的有力例证!
从字形上看,水族文字“人”字(详见上图三)分明就是汉字“大”字的变体,略有区别的是,汉字“大”字是曲肘向下,而水族文字“人”字则是曲肘向上。既然汉字“大”字像人形,水族文字就稍微变换一下姿势,用来表示“人”,其形义来源和因袭关系已昭然若揭,还玩什么“远古”与“神秘”,说水族文字与甲骨文同时产生,甚至可能比甲骨文还早?这是孙子与爷爷争高寿——瞎摆老资格,简直是自欺欺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三都水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宋晓君先生在创作《水族铜鼓舞》时,就是成功地融入了民族文化元素,把水族文字“人”字这一造型渗透于各个动作之中。无怪乎,在描写水族铜鼓舞的动作特征时,《水族铜鼓舞探源》的作者这样写道:“舞蹈者着装整齐之后,便敛聚心神,表情肃穆,以铜鼓为中心,以骑马蹲裆式,屈肘抬臂、五指撑开、掌心向前的基本姿态起舞,随着铿锵有力的浑厚的铜鼓和皮鼓的音响节奏,人们时而屈肘‘骑马’蹲跳,时而急速旋转穿插跃飞,做着大字蹲、大字偏、大字转、大字飞、大字托掌转、大字冲、大字冲穿转等动作。”
没有文字学基础知识的人,当然看不出水族文字“人”字与汉字“大”字之间的渊源关系。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明就里的人,乍一看,水族文字“人”字,的确像一只张牙舞爪、活蹦乱跳的青蛙。于是乎,《水族铜鼓舞探源》的作者根据水族迁徙古歌中叙述水族先民曾经在两广生活的历史,便想当然地将这一民族文化元素与广西花山岩画中的怒蛙图嫁接拼凑起来,得出“水族源于骆越,有蛙崇拜习俗”的结论。这些专家,研究学问的眼界何其狭窄,而想象力却丰富得惊人!
该文作者还说:“作为祭典舞蹈,在今天的的实际生活中,仍广泛应用于丧葬活动之中,而且由于祭祀对象男女有别,而要求铜鼓演奏者有不同饰物以祭亡灵。若祭奠者为男性,则铜鼓演奏者需手脚戴马响铃,以示亡人升天后威风凛凛,跨马奔向天庭;若祭奠者为女性,则演奏者戴牛字头饰,以示亡人升天后有牛可耕,以温饱衣食的祈愿。”
《易经•说卦传》第八章:“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易经•说卦传》第十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因此,水族葬礼,父丧椎马(公马),母丧椎牛(母水牛),其祭祀文化正源于此。这是“水汉同源”的又一有力例证!作为祭典舞蹈,水族铜鼓舞演奏者在演奏时,针对男性,要手脚戴马响铃,针对女性,则戴牛字头饰。这在文化渊源上不是一脉相承了吗?这就是水族文化研究专家不读中华文化元典所付出的学术代价!
接下来,咱们举一个放洋屁的例子。贵州省水家学会群里有一位是民族学和人类学专业出身的专家,应和着说,自己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仅仅学了一些皮毛,不敢探索水族源流问题,这当然是自谦。既然取得了民族学硕士学位、人类学博士学位,决不可能只学了一些皮毛,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学得比较精深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民族学和人类学方面,不管你学得如何博大精深,对于解决民族源流问题而言,始终是皮毛,不能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研究民族文化方面,这位专家是不会相信语言学的,就算今后他转而相信语言学,下苦功夫把语言学,尤其是音韵学彻底弄通了,也不能顺畅而轻松地解决水族源流问题,因为他缺乏水族语言与文化的原生体验,而且从年龄上讲,早已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这好比骡子,虽然身强体壮,但不幸得很,先天注定没有生育能力!
这位专家的水族文化研究文章,我读了两篇:《水族端节祭祖仪式与忌油圈——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告村板鸟寨为个案》,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总第197期;《水族的端节与社会组织——以三洞乡为例》完稿于2006年6月3日,是作者在西南民族大学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时写的学位论文。这两篇学术论文,在缺乏水族语言与文化原生体验的人看来,大量援引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而且前文发表于权威学术刊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后文是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一定是两篇宏文。而在具有水族语言与文化原生体验的人看来,则是满纸垃圾!这两篇学术论文,今后水族内部一定会有人专门写文章来进行系统的批驳。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暂且从《水族的端节与社会组织——以三洞乡为例》抽取个别地方来进行商榷,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例如:“还有的人用姓来划分家族,但水族的姓与汉族的姓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水族的姓是借汉姓,所以同姓不等于同家族。因此,要了解水族的社会组织需要从它的内部来区分,而不是用汉族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划分。”“而第三批的端节,现有的板告端坡、良村端坡所辖的区域,也相对集中,姓氏上也都借用‘韦’姓,从当地以姓等同家族的认同上看,他们之间在很久以前也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第二批的群力端坡,尽管也姓‘韦’,在认同上更趋同于其批次内的成员,而以板告、良村等的韦姓较远。”
水语属于汉藏语系,与汉语有亲缘关系,这是目前语言学界公认的事实。通过钻研音韵学,我们初步知道,水族民众天天都在讲地地道道的古华语,水语其实就是古华语方言。只要读过林连通、郑张尚芳主编的《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就知道水族人民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余”“予”“吾”“台”“尔”“汝”这些人称代词,只是由于语音古今演变,大多数人不懂音韵学,习惯于以今律古,不觉察出来而已。只要你认真阅读先秦典籍,就会发现,水族从古至今一直传承下来的习俗,都是渊源有自的。认为一个天天讲古华语方言和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借用汉姓,水族在借用汉姓之前,一直是有名无姓,这简直是瞎扯淡!这位专家也是水族,你认为你家姓氏是借用汉姓,那是你们一家人的事,千万别扩大到整个水族上来。水族是个弱小的民族,在民族歧视特别严重的传统社会里,为了解决人口繁衍和民族存亡问题,水族先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早已破姓通婚,今天水族地区哪里会有“以姓等同家族的认同”?这更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瞎扯淡!
例如:“在三洞中学,老师们的吃端基本不带任何礼物送主人,都将吃端看作应该有的权利。不论组织到当地老师家还是某位学生家吃端,多数人是空手去的,不带任何礼物,如果你带了都要偷偷递给主人,最好不要让其他人见到,不然他们心里就会不太高兴,认为你是搞特殊,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男性到家就下鱼塘打鱼,抓起准备好的鸡鸭就宰杀,女的帮助主人做饭、洗菜、烧水等。没事做或不想做事的,就几个坐到一块打扑克、打麻将等,就像主人家是茶楼一样。酒足饭饱后就扬长而去,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会跟主人道谢。”
只要认真阅读《周礼》《仪礼》《礼记》等传统礼学书籍,并仔细对照观察水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之道,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在传承传统礼俗方面,水族虽然不是做得最好,但决不会是做得最差的民族。以点代面,以偶然当必然,把水族民众的道德素质写得如此低下,实在有失公允!
例如:“主人可以借吃端来表达他们的某些意愿。特别是领导到家吃端,酒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向领导提建议或个人要求,只要合理,其他同事就会声援。同时吃端还可以扩大人际关系。在水族聚居区,主人介绍客人最详细具体的时候一般在酒到一定量后,如果某单位人事处领导及其下属到王某家吃端,这些人估计只知道或认识王某的哥哥,到家时王某只是简单的提及,其余家庭成员也不会主动与这些客人有较多的交谈,但在酒桌上一切都变得热情起来,王某的哥哥详细介绍这些客人,其他成员就借机敬酒来了解客人的相关信息,在不断的敬酒中建立相互间的个人关系。”
难道水族民众过节待客,就是为了设局,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水族人民的良心都是这么坏的吗?把水族民众过端节的目的和动机写得如此势利和庸俗,居心何在?幸亏这篇学术论文目前受众面较小,知者不多,骂声较少。如果在手机上竞相转发,一传十、十传百,形成蝴蝶效应,激起公愤,我敢说,今后作者到水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一定会被民众围攻骂娘!藉此可见,当今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其素质和水平是何等低下!
列举大端,可概其余。这就是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在民族文化研究中流于皮相的有力证据!如果说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能够从实质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历史学和语言学可以撇开不用,为什么水族文化研究开展四十多年来,一直无法自圆其说,陷入泥潭、不可自拔?为什么仅凭“suī”这个读音,就跑到河南睢县去认祖归宗?此事目前已成为天大笑话,随着时间推移,今后将会成为千古笑话!
由于昧于历史学和语言学,这些权威专家根本不知道,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棵大树上的各条枝丫,滋养着这棵大树茁壮成长的,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只是有些枝丫向阳,光合作用强一些,长得茂盛,有些枝丫背阴,光合作用弱一些,长得稀疏。在他们心目中,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从远古以来早就同时并存,只是都潜伏在历史的榛莽深处,有实无名,后来首长一声令下“起立”,全部齐刷刷地站立起来,终于名副其实。又像现代农业种植大棚里的幼苗,同时播种,在农艺师的湿度和温度操控之下,一夜之间,全部长出地面。所以,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之间,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是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的,即使在语言上有联系,那也只是借用汉语而已。这样一来,就必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国内相关少数民族在借用汉语之前,都没有语言,都不会说话;如果都会说话,那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言?难道这些少数民族是从天而降?或是以前都各自在海洋上漂流,因飓风翻卷而聚在一起?在某些不懂、不信语言学的专家看来,上古、中古、近代的华语是各不相同的,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渊源关系,就像炉灶一样,以前用柴火炉,后来用液化炉,现在用电磁炉,迥然有别。以这样的观点和眼光,仅凭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来进行民族研究,无怪乎,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最简单、最容易的事业,只要能够识字,能够开展田野调查,能够记录民间传说,就可以从事民族文化研究了,无需接受学术训练和学术规范,更无需通过钻研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去阅读那些文字古奥、佶屈聱牙的中华文化元典!
中国马屁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清代游戏主人《笑林广记·颂屁》:“一士死见冥王,自称饱学,博古通今。王偶撒一屁,士即进词云:‘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王喜,命赐宴,准与阳寿一纪,至期自来报到,不消鬼卒勾引。士过十二年,复诣阴司,谓门上曰:‘烦到大王处通禀,说十年前做放屁文章的秀才又来了。’”在这些权威专家四十多年的连环屁声中,水族读者早已厌闻其声、恶嗅其味,但都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有我生性耿介,既不愿意闻屁声,也不愿意嗅屁味,更不喜欢拍马屁,必须提出异议。这些学者,平时以权威专家自命,习惯了鲜花和掌声,只喜欢听喜鹊报吉,不愿意听乌鸦报凶。所以,一听到有人提出异议,而且是直话直说,触到自己的痛处,就气急败坏、大发雷霆。这是由于长期被读者惯坏了,他们的脾气与名声形成正比。以前,水族读者尚未觉醒,族外人反正也读不懂,这些专家无所顾忌,信口开河,随意发挥,自己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如今,水族读者已经觉醒,开始提出不同意见,水族文化研究将会迎来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清代诗人龚自珍《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有句云:“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这些专家还自我陶醉在昔日的学术殿堂里,根本不感觉到自己的学术末日即将来临!
《晋书·阮籍传》:“(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奉劝这些权威专家降低身份、消除脾气,既认干爹、更认亲爹,既认朋友、更认弟兄,敬畏学术、尊重元典,手不释卷、学而不厌,否则,继续信口开河、率尔操觚,制造文化垃圾,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庄严肃穆的学术法庭,你们将接受严峻的学术审判和学术清算。即使你们侥幸获得善始,也决不会得到善终!